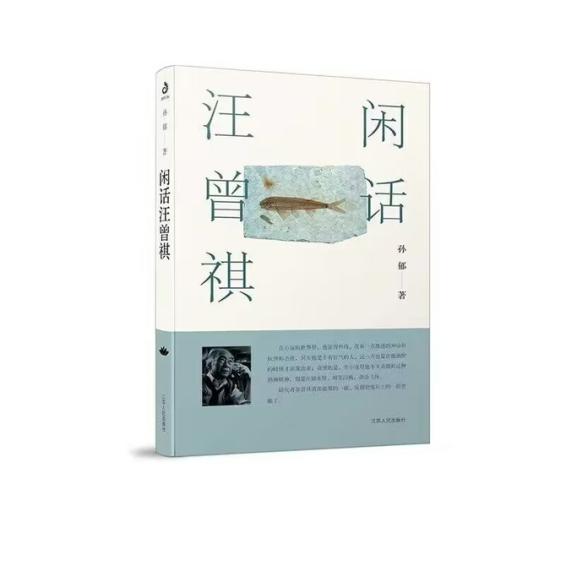学者孙郁:
1997年3月,孙郁(右)与汪曾祺(左)、林斤澜(中)在一起。
《闲话汪曾祺》
鲁迅、沈从文、张爱玲、汪曾祺、孙犁等人的作品,一直被一代又一代年轻人阅读,表现出极其茂盛的艺术生命力。有统计表明,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,他们是去世后作品被再版次数最多的几位作家。这是为什么?他们有何共通之处?在研究鲁迅、汪曾祺多年的人文学者孙郁分析看来,除了他们的作品里有智慧和人性的关照之外,在审美形式上,这几位文坛上的“明珠”作家都“把中国的传统与域外现代的艺术结合得较好,或者说是融会贯通”,“他们都是杂家,又保持了诗人般的纯净”。
2020年是汪曾祺诞辰100周年,400多万字的《汪曾祺全集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,引发一波不小的汪曾祺热。除此之外,近些年解读、诠释汪曾祺的各种著作层出不穷,形成一股持续的汪氏热潮。其中,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郁对汪曾祺的解读,备受业内和广大读者认可。2022年末,孙郁的新书《闲话汪曾祺》推出。书中对汪曾祺其人其文,展现出新颖独到的解读角度、见解,令人惊喜。
汪曾祺的文章好,是公认的。但要说出来“为什么好”“如何好,是怎么个好法儿”,并不容易。孙郁对汪曾祺的“闲话”,从历史纵深到同代横向对比,多个方向话出了汪曾祺的人文世界的众多秘密。
尤为特别的是,孙郁对汪曾祺人文世界的探究,是以点带面,将汪曾祺放在文脉长河中分析其独特之处,对与汪曾祺相似或者差别很大的同代或者前辈、后辈作家进行对照解读,对张爱玲、周作人、沈从文、废名、赵树理、老舍、阿城等人也展示了非常精辟独到的理解,让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更深的感知。
汪曾祺在世前,孙郁曾去过他家里拜访,有一个印象很深刻,“书不多,画倒不少。和他谈天,不怎么讲文学,倒是常常聊起民俗、戏曲、县志一类的东西。这在他的文章里也有体现。他同代的人写文章,都太端着架子,小说像小说,散文像散文,好像被贴了标签。汪曾祺不是这样。他在一定程度上是个杂家,深味文字之趣,精通杂学之道,境界就不同于凡人了。”
晚清后的文人,多通杂学。鲁迅、周作人、郑振铎等人皆然。在孙郁看来,汪曾祺有杂学,但不是研究家的那一套。“他缺乏训练,对一些东西的了解也不系统,可以说是蜻蜓点水,浮光掠影。但因为审美的意识含在其间,每每能发现今人会心的妙处,就把古典的杂学激活了。汪曾祺在阅读野史札记时,想的是如何把其中的美意嫁接到今人的文字里,所以文章在引用古人的典故时,有化为自己身体一部分的感觉。”孙郁说。
通常观点会认为,作家总要多懂人情世故,博学多才。但耐人寻味的是,汪曾祺的阅读量不算太大。可是他读得精,也用心,民谣、俗语、笔记闲趣,都暗含在文字里,好玩极了。他喜欢《梦溪笔谈》《容斋随笔》《聊斋志异》这样的作品。这跟汪曾祺读书的一个观点是一致的——他不主张作家像学者似地读书,因为那样不易培养出兴趣来。在《谈风格》中,汪曾祺写道:“我不太主张一个作家有系统地读书。作家应该博学,一般的名著都应该看看。但是作家不是评论家,更不是文学史家。我们不能按照中外文学史循序渐进,一本一本地读那么多书,更不能按照文学史的定论客观地决定自己的爱恶。”
在孙郁看来,汪曾祺这个看法与鲁迅很像。“在《随便翻翻》中,鲁迅谈到了浏览书籍的心得,也有类似的感受。细看汪曾祺的书,可以看出其兴趣极广。烹饪、书法、方言、水墨画、家具、鸟虫、考古等,时常入眼。不过他发文章都不专门,浅尝辄止,印象、感悟式的居多。偶尔也有颇见功力的小品,笔力绝不亚于那些专家。他有一篇考证宋朝饮食的文章,笔法老到,资料爬梳中趣味横生。还有一些记录民风的短札,从乡邦文献里寻找遗物,时有让人意外的惊喜。从他与几个学者的交往里,能发现考据的乐趣,对辞章、义理也颇有研究。那些死的资料,经由其诗意的笔触,都活了起来。”
中国文坛有“故事新编”的传统。鲁迅曾写过《故事新编》,林语堂也用英语改写过《虬髯客传》《莺莺传》《南柯太守传》等中国古代小说。汪曾祺晚年做文学实验——改写蒲松龄的聊斋。他的小说集《聊斋新义》备受年轻人喜爱。有评论者说,新生事物层出不穷,汪曾祺选了另外一条路——把旧的创造出来了。
汪曾祺改聊斋,是用现代意识发掘其未尽之意。比如《瑞云》的原著结尾,在贺生的“帮助”下,瑞云的脸又恢复了光洁。这个故事原本的主题是赞扬贺生的“不以媸妍易念”,这是道德意识,不是审美意识。歌德说过,爱一个人如果不爱她的缺点,不是真正的爱。在汪曾祺的改写中,当瑞云的脸晶莹洁白,一如当年,贺生却不像瑞云一样欢喜,反而若有所思。这样一改,就是一个现代意味的爱情故事了。
汪曾祺的《聊斋新义》,在孙郁看来,“流动的是清妙的韵致,从头开始,皆被优雅的旋律笼罩。贾平凹说他是‘文狐’并非没有道理。他写离奇的故事,不都含巫音,可谓甜意的播散,美感把黑暗遮掩了。”
汪曾祺不只写小说、散文,会画画,还是京剧《沙家浜》的编剧。这也给孙郁解读其文学秘密提供了一个思路——汪曾祺的虚构作品往往具有戏曲、小说混血特质,“我们读他的书,常能发现那些传神的地方像旧戏的演绎,流动着飘忽悠远的情思。戏曲的空灵和平实,是中国艺术的遗产,汪氏从那里学到遇到了只可意会、难以言传的东西。”
由于汪曾祺学识驳杂、趣味丰富,被不少人称为“最后一个士大夫”。在孙郁看来,汪曾祺的本质是一个学问家,“但他的学问不都是书本上的知识,还有生活的道理。他没有把这些学究化,而是在诗意与风俗画的感性描绘中,不动声色地呈现出来。我们有时候能够感受到他跟柳宗元、苏轼的一些文字相通的片段,有时候能读到他跟张岱、袁宏道、袁宗道这些人内心相通的句子。但是他又有现代性,他并不是回到古老的士大夫文化的秩序里,他有现代精神。”
文学是语言的艺术。汪曾祺小说一大吸引力就在于他的语言风格:简朴、大气、有味道。“表面是大白话,支撑这个白话背后的是文言文。他把我们先秦、两汉、魏晋、唐宋、明清一直到近现代,不同的学人、不同的作家、艺术家的词章的好体验,部分地吸收到自己的文章里面。所以读他的书,有的时候虽然很短,但是微小之中、方寸之间见广远,这真是使汉语得到一次解放。原来文章可以这样写,小说可以这样写。”孙郁特别看重汪曾祺对汉语文学语言的贡献,认为汪曾祺把京派儒雅的、散淡的、趣味的话语结构召唤出来,“他重新衔接六朝文的趣味、唐宋文的美质、明清文的韵致。而且把俗语雅化了,大雅里面有大俗,非常不得了。这是鲁迅也没有的特质。”
人都不是万能的。作家也不例外。孙郁也指出了汪曾祺的短板之处。比如,同时代的张爱玲懂得英文,能读出洋人的妙处,而汪曾祺则一直在古老的母语世界里,与西洋的艺术总归是有隔膜的。汪曾祺曾说,自己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学好英文,导致读人读世的目光受限。封面新闻记者张杰图片由孙郁先生提供
孙郁,1957年生,曾任《鲁迅研究月刊》主编,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。2002年到鲁迅博物馆主持工作并担任馆长。2009年起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。长期从事鲁迅和现当代文学研究。主要著作有《闲话汪曾祺》《鲁迅忧思录》《鲁迅与周作人》《鲁迅与胡适》《鲁迅与陈独
秀》《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》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