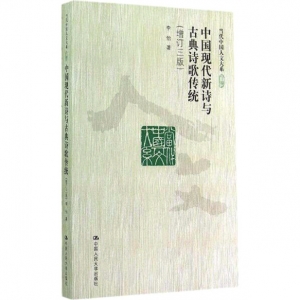川大文新学院院长、博导李怡:
以诗之热情,做文之学者
《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》
李怡(中)与学生在一起。
李 怡(左)与恩师王富仁(2000年)。
2022年6月,封面新闻记者在四川大学文新学院面对面采访李怡教授时,恰逢一位博士在读学生来找李怡谈即将开题的一篇论文。在认真听学生讲述问题、困惑之后,李怡给出了专业的意见和建议。记者发现,李怡跟学生多次强调一个事儿——写论文首先一定要“非常清楚自己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,发现真问题之后,才谈得上别的。”
在学术界浸润多年,练就了李怡很强的问题洞察力,“如果一个人对着一个似是而非的假问题,研究来研究去,意义不大,浪费生命。”他屡次跟自己学生讲:“如果你能提出一个值得探究的真问题,哪怕论文得出的结论别人不同意,也一定会得到尊重。”
这么多年,身为导师带学生做论文,李怡发现,“一个真做学问的人,肯定不是等到论文开写的时候,再去绞尽脑汁想一个问题或者课题。问题、课题的出现,应该是伴随着人生自然产生的一种体会。只要一个人对人生还有所理想,有所追求,还愿意思考,就一定会遇到真问题。”
做学问之前
先对故事、文学产生爱
除了鲁迅研究,中国现代诗歌是李怡用心血耕耘的又一研究重地。在常见的宏大叙事路径之外,他偏爱对个体诗人和具体文学作品进行解读。这使得他的研究带有浓厚的“文学体验”色彩。比如在研究郭沫若、徐志摩、李金发、卞之琳、何其芳、戴望舒、艾青、绿原、穆旦、梁宗岱等人时,李怡会通过自己的文学感受提出一些与过去迥然有异的看法:郭沫若的内在矛盾,徐志摩的重构古典情趣等等。细致的文学阅读给了李怡丰富的艺术体验,推动他走进了一个又一个文学家的精神世界,给了他从事学术研究的最“基本”的财富。热爱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。李怡很感念自己在还没有接触到文学理论大道理的时候,就先从感性上对故事、文学产生爱,“这非常重要”。
每一个对文艺善感的灵魂,往往都有一个少年时代的启蒙师长。李怡想起他的外祖父,尤其是当数学老师的舅舅,“我舅舅数学非常好,同时他的文学才华也不弱于数学,是一个讲故事的天才。舅舅曾经给我讲《西游记》的故事,每天晚上讲。”
受舅舅影响,李怡数学也学得很好。从初中到高中,“就没有遇到把我彻底难倒的数学题。”作为文学学者,他最早发表的文章不是文学作品,也不是文学研究论文,而是关于数学几何题的证明方法,“初中的时候发表一篇,高中的时候又发表了一篇。当时发的是重庆一家正式的公开发行学术刊物。”
真正深入文学的世界,是李怡1984年考入北师大中文系之后。怀揣着作家梦的他写剧本、写小说。在图书馆里读着一本又一本的现代诗集,自己也开始在纸上写起来。在这期间,著名诗评家谢冕先生应蓝棣之老师之请来北师大演讲,那带着“朦胧诗论争”岁月所特有的情绪和在此以后蓝棣之老师同样富有情绪感染力的“现代诗”选修课,更是大大地增强了李怡对诗歌的兴趣。
不过,此时此刻的诗歌与文学之于他,全是情智的相通,还与“学术”无关。现在想来,这种较长时间的自由幻想与自由情感的体会,与当今某些功利主义的教育拉开了距离,让李怡真切地感受到了“情感体验”的意义。“这难道不就是一种幸运,甚至一种财富?”李怡回忆道。
真正的学术
可以像诗歌一样动人心魄
在大学里痴迷写诗、小说的李怡,慢慢发现,要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找到自己的独创性,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。恰在此时,李怡遇到教他现代文学的恩师王富仁先生,“他向我展示了一个现代文学学者可以具有的魅力。我就想,那我也可以向着这个方向前进,通过努力找到自己的路。我好像就开始找到了自己。”
也是在这期间,王富仁教授在《文学评论》发表了《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——<呐喊><彷徨>综论》。这篇文章在1980年代震动学界,引发一股强劲的鲁迅热。李怡至今还清晰地记得,当时他在图书馆阅读《文学评论》时的那份不可遏止的激动,“我感受到了一种真真切切的极具思想力度的学术的逻辑。原来真正的学术,也可以像诗歌一样动人心魄!”
在王富仁老师的指导和影响下,李怡很快就学会用论文表达自己观点的方法。几个月之后,他将自己的学术处女作《论<伤逝>与现代世界的悲哀》呈至王富仁老师。一年之后,更将一篇三万字的长文《论中国现代新诗的进程》送到了《文学评论》编辑部王信老师的手中。这两篇文章先后发表在《名作欣赏》与《文学评论》上。李怡由此走上了文学研究的“学术”之路。
李怡的创作才华并没有被写论文、教书所湮没。不管是听他讲课,还是看他的论文,都能看到李怡思路和方法的别致。“学术表达有高度的规范性。因为做学问、写论文,最主要的功能是与同道交流,要遵守一个比较稳定的话语体系。但是在种种学术规范限制之下,依然可以做出新意,可以表达自己鲜活新颖的思想。”他说。
李怡想起自己大学刚毕业的时候,在乡下中学教书期间,坐在办公室里,在被浓密的夜色所包裹的灯光下,耐心细致读鲁迅《故事新编》的情形。读后激动不已,促使他用理论性质的文章记录下了一次又一次的心动。“我曾经将这些阅读的体验低吟给身边新识的朋友,然后在第二天走半小时的田间土路再搭船渡过洲河,通过小镇邮局将其寄往北京的《鲁迅研究月刊》。没有电子邮件的年代,空间的距离令人怅惘、令人孤独,但也给人诸多反观自我的机会,没有电脑快速打字的年代,每一笔文字的刻画都仿佛凝结着人生的见证。文学如何让我们体验人生,人生又如何需要文学的拥抱,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,依然让我记忆犹新!尊重自己的文学感受,将学术纳入到生命体验的过程之中,我们才能有所质疑,有所创立。”
为师的三种境界:
经师、业师、人师
在李怡的学术乃至人生道路上,导师王富仁的影响深远。记者请他谈谈心目中的恩师,李怡沉吟半晌,先是说出这么一番话:“师者分为好几个境界:经师、业师、人师。能够把书教好,带领我们阅读中外文化经典的,叫经师。这是一个好老师。但是仅仅做到这一层面,还是表面的。更重要的是,通过阅读经典教弟子能够形成自己的事业,这个称之为业师。能够成为经师和业师,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。更罕见的是,带领学子不断自我反省,自我超越,最终让学子理解人生,思考生命。这样的老师被称之为是人师。在我而言,王老师不仅是经师、业师,更是人师。在他的身上,我能感觉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巨大的精神魅力,是学生的一盏灯塔。”
王富仁曾在他的一本著作里,把鲁迅称之为“中国文化的守夜人”。在李怡看来,“王老师自己也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守夜人。在我们默默前行的时候,在我们人生和事业上遇到困难需要重新自我反省、自我思考的时候,他就像黑暗中的一盏灯,照亮了我们,也温暖了我们。”最后,李怡也不忘补充,其实很难用几句话完整概括,“只能用文学性的比喻,来描述王老师作为一位师长所给予我们生命的意义。”
从重庆到北京,再到成都,促发了李怡对地域与文学之间地理关系的浓厚兴趣。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,近些年李怡重点思考的一个问题是:一个作家跟其所处的地域是怎样的关系?用学术的话来说就是,从“地方路径”的角度,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进行更细节的挖掘。比如张爱玲与上海、萧红与东北、李劼人与成都。在李怡看来,一个人,当然也包括一个文学家,不会抽象生活在一个概念里,而是实际生活在一个非常具体而微的地域环境里。一个人周边、非常局部的环境、风土人情往往直接影响他的思维、情感以及交往方式。生存的苦恼、困境和方式成为文学非常重要的基础。
2020年,李怡在一篇发表在《文学评论》中的论文《成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地方路径问题》中,特别分析了李劼人、张爱玲、老舍的文学世界与其长期居住的具体城市之间的关系。最终,他得出一个观点,中国现当代文学是由一条一条的地方路径最后汇通而成的,“并不是先有一个抽象的中国现代文学,然后这个文学在上海有表现,在北京有表现,在成都有表现。而是先有了现代文学上的上海路径、北平路径、成都路径……最后这些路径综合起来,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现代文学上的中国路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