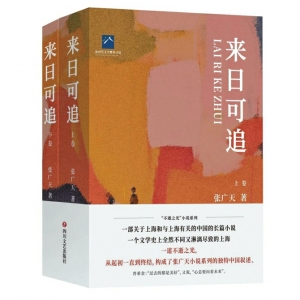“奇人”张广天:在当代语文的秘径中追逐不逝之光
张广天 四川文艺出版社供图
《来日可追》 四川文艺出版社供图
张广天称得上是一个奇人。他1966年出生于上海,学的专业是理工农医类的医科,组过摇滚乐队、民谣乐队,四处吟唱诗歌。上世纪90年代初他移居北京,曾以音乐家身份为电影《离开雷锋的日子》《摇啊摇,摇到外婆桥》《敌后武工队》等多部电影、电视剧创作音乐。不过,他作为先锋戏剧家的身份在圈内也广为人知,从2000年的《切·格瓦拉》,到后来的《鲁迅先生》《圣人孔子》等,曾引发戏剧艺术界的震动。如今,张广天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,担任导师的方向是“方法论叙述与表演”。
近几年,他开始在文学写作上发力,呈现井喷的创作状态。从2012年至今11年,出版五部长篇小说、两本诗集和一本叙事长诗、一本学术著作,每一部作品都料质充实,形式新颖。比如《妹方》《南荣家的越》《玉孤志》《手珠记》《既生魄》《甘伯记》等作品,因风格奇特、诗意浓郁、思想深邃,备受瞩目。
他书中的中国叙述 既向着古代也朝着未来
2023年年末,作为中国作家协会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支持项目之一,张广天的第五部长篇小说——两卷本近八十万字的长篇小说《来日可追》由四川文艺出版社推出。四川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吴坤说:“从《妹方》《南荣家的越》一直到《来日可追》,张广天的小说始终在一条当代语文的秘径中探险,构成了独特的‘中国叙述’。这种中国叙述,既向着古代,也朝着未来,古人、今人和少年,都由着文学的努力而指向未来之日。这或许就是最近刚出版的这本《来日可追》的目的——追逐一道不逝之光,成为他小说的系列。”
纵然涉足领域广泛,身份交错,但张广天说,五十岁以前,他始终只是文艺的小学生,此前的音乐、戏剧,都是调皮的孩童玩耍。如今他开始敞开心扉,潜心写作。2023年,张广天生了一场病,回到上海养病。他回忆起自己少年时代在上海所受到的精神滋养,遇到的不同的人。这些回忆化作他笔下虚构的人事:亨利路上会说上海话的白俄薇拉阿姨,上海梧桐树下的艾伦·金丝堡,上海周边小镇上身怀绝技的郎中……
他发现,“这些年我去了中国北方、西方、东方的城市,不管到哪,我发现我的思维方式还是上海人的。”站在黄浦江边看轮船听汽笛声,他想到了很多往事,物非人是,“我还没有变。”
用令人眼花缭乱的笔法 书写一部献给上海的情书
在《来日可追》开篇的序言中,张广天写道:“来日,就是将来的日子,未来的日子,也有说是来过的日子,来到的日子。这些时日,无论是来到的还是未来的,都不是现在。普希金说:‘过去的都是美好’,又说,‘心总要向着未来’。那些来日,因向着未来的心,总是美好的。”
《来日可追》共分为四辑。第一辑“中心区”,有《亨利路上的薇拉阿姨》《尤佳》《玫瑰屋》《每一条归途都通向未来》四章,以上海市区生活为叙述核心,写白俄的钢琴师、少年的情人、美丽而奇幻的玫瑰园以及老克勒的执守和惆怅。第二辑“边缘与远方”,有《下海滩》《没膝的卷耳令你昏醉》《寂寥少年》《火车》四章,写被遗忘的角落和人群,另一个城市的明星故事,一个工业锈带的生锈记忆。第三辑“这些影儿都挡了一下时光”,有《金虎撑》《独鳞汤》《飞英台玉碎》《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》等八篇。第四辑《父亲》是一首叙事长诗。
书中从上海的中心区写到边缘区,又写到与上海有关的远方,最后回到个人,回到父子的对话,尾声是一首长达几千行的长诗,从父到子,似乎比之前所有地方都要远。有评论说:“这不是一部连续的小说,而是一种精神地理学:出场的是一个一个的人,但主角却是上海。所以,毋宁套用一句滥俗的评价:这是一部献给上海的情书。”
写作是物事情理交织的过程 回到中国文学的原叙述状态
读《来日可追》的一大感受是,文笔与见识一路迸溅,很有阅读的收获感。在张广天看来,写作基本上是一个物、事、情、理各路交织的过程,不应该是叙事、抒情和议论的割裂。“我们读《淮南子》《庄子》《史记》这些作品,怎么归类呢?为什么要归类呢?人是一个整体,表达也应该是一个整体。我尝试回到中国文学的原叙述状态,即在西学分门类以前的状态。”
这几年,张广天在写作上开始发力,有人说他转型了。张广天不认为如此,“我一直就是一个写作者。只是,我所认识的文学,或者与许多人想的不一样。我热衷于文学,从少年时代起始终不变,但我绕道走了。在以往的30多年里,写作至少对我来说是件复杂的事。我需要通过在别的领域中取得成绩然后获得文学的话语权。我需要学习从各个已被分解的门类中,去找写作最有价值的技巧。比如从音乐中学习节奏,从戏剧中学习冲突。另外,我也不希望去攀越那么多文学的师门和圈子,我要获得直接写作的能量,摆脱人脉、资源和信息的束缚。从此,我可以安心写作、不断写作。”
文学家应该致力追寻 语言有多大可能性及其边界
2023年岁末,在《来日可追》出版之际,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与张广天有一番深入的采访、交流。
记者:在很多人的印象中,你是做先锋戏剧的先锋派,这几年你集中写小说,表现出旺盛的创作力。比起你创作涉及到的其他艺术形式,文学的独特性是什么?
张广天:我的戏剧是先锋的,我的文学当然是先锋的。我的戏剧是先锋之后的,就是经历过先锋之后的反思,所以,我的文学也是先锋后的。于我个人而言,文学不是什么独特性,而是我的趣味。我认为,文学是天下最难的一桩事,比科技、金融以及其他门类艺术都要难得多。一个人能够坐下来写,不敷衍地写,以写来推动现实,没有比这个更难的了。这个世界,虽未必是语言的事实大于事实的事实,但终究是语言的事实要掌控事实的事实。所有专业都是语言的呈现,是语言的结果,“怎么说”比“是什么”有决定性作用。我对孩子说,读字足矣。几千年来,我们都是学文学的,以文学为真学问,读文学,考文学,半部论语治天下。
记者:《来日可追》的文字风格审美感很高。如果说《妹方》被称为“珠玉之作”,那么《来日可追》可称得上是“玫瑰之作”。你如何看待语言对小说的重要性?语言风格与情节之间应该是怎样的关系?
张广天:关于文学,长久以来有一种深深的误解,就是“经历说”,仿佛各样丰富复杂的经历是文学创作的基础,好像经历够惨够复杂就会当然地生成好作品。还有一种观点,就是“大题材”说。从文学的本体而言,文学是语言的艺术(在中国还要多一样,叫语文的艺术)。语言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,它的边界在哪里,这是文学家应该致力追寻的。简单通俗地说,就是如果你写的那个故事太故事了,就没有文学了。文学不是故事艺术,文学是语言艺术。如果一个故事似是而非,或者没有多少故事,但语言以其艺术魅力把它讲得头头是道,是谓文学。
另外,今天是一个被信息淹没的时代。信息不是语文,语文包含信息又大于信息。实际上今天许多作家的写作,AI是完全可以取代的。我们用文学来开求生存的路,消遣、传播、发泄,我们把文学严重弄丢了。不过,这个不要紧,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优秀的文学。懂得文学的人还是有的。
记者:你的新小说名字叫《来日可追》。在序言中写“那些来日,因向着未来的心,总是美好的”。这种对“未来”充满理想主义的时间观,是怎么形成的?一个普通人都会面对生命肉身的衰老,时间不可逆,多多少少会有悲伤的感觉。你有怎样的体会?
张广天:人生既有少壮衰老,必有各时之美,而且青春与耄耋是相对的,好比春夏秋冬,有寒必有暑,没有这个过程,那就不叫生命了,是不完整的切片了。你能想象一个人独独把青春切下来过吗?所以,首先,这是一个时间观。人不能被时间捆牢,唯恐落后于时代。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不幸,就是赶时髦追热度,不幸热度从一热三个月快到一热才三秒钟。一个热搜,三秒之后就被下一个覆盖了。我说到“来日”,一是指来过之日,二是指未来之日。有许多过去的事情在未来还会发生,以为一件事情新过另一件事情,这是想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