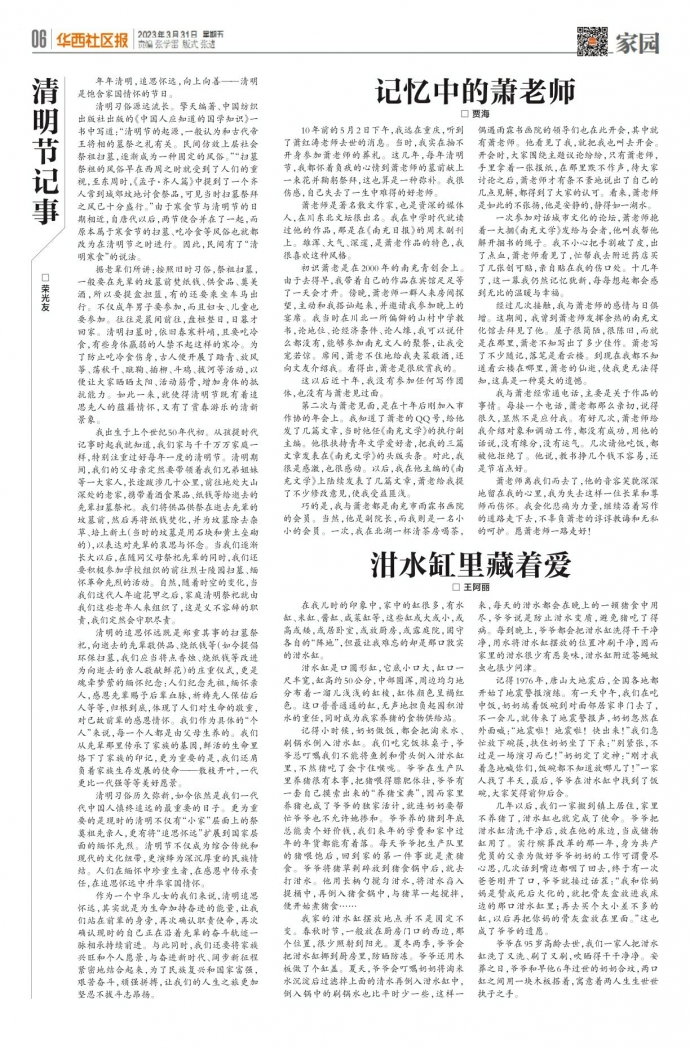泔水缸里藏着爱
□王阿丽
在我儿时的印象中,家中的缸很多,有水缸、米缸、酱缸、咸菜缸等,这些缸或大或小,或高或矮,或居卧室,或放厨房,或露庭院,固守各自的“阵地”,但最让我难忘的却是那口敦实的泔水缸。
泔水缸是口圆形缸,它底小口大,缸口一尺半宽,缸高约50公分,中部圆浑,周边均匀地分布着一溜儿浅浅的缸棱,缸体颜色呈褐红色。这口普普通通的缸,无声地担负起囤积泔水的重任,同时成为我家养猪的食物供给站。
记得小时候,奶奶做饭,都会把淘米水、刷锅水倒入泔水缸。我们吃完饭抹桌子,爷爷总叮嘱我们不能将鱼刺和骨头倒入泔水缸里,不然猪吃了会卡住喉咙。爷爷在生产队里养猪很有本事,把猪喂得膘肥体壮,爷爷有一套自己摸索出来的“养猪宝典”,因而家里养猪也成了爷爷的独家活计,就连奶奶要帮忙爷爷也不允许她掺和。爷爷养的猪到年底总能卖个好价钱,我们来年的学费和家中过年的年货都能有着落。每天爷爷把生产队里的猪喂饱后,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煮猪食。爷爷将猪草剁碎放到猪食锅中后,就去打泔水。他用长柄勺搅匀泔水,将泔水舀入提桶中,再倒入猪食锅中,与猪草一起搅拌,便开始煮猪食……
我家的泔水缸摆放地点并不是固定不变。春秋时节,一般放在厨房门口的西边,那个位置,很少照射到阳光。夏冬两季,爷爷会把泔水缸挪到厨房里,防晒防冻。爷爷还用木板做了个缸盖。夏天,爷爷会叮嘱奶奶将淘米水沉淀后过滤掉上面的清水再倒入泔水缸中,倒入锅中的刷锅水也比平时少一些,这样一来,每天的泔水都会在晚上的一顿猪食中用尽,爷爷说是防止泔水变质,避免猪吃了得病。每到晚上,爷爷都会把泔水缸洗得干干净净,用水将泔水缸摆放的位置冲刷干净,因而家里的泔水很少有恶臭味,泔水缸附近苍蝇蚊虫也很少问津。
记得1976年,唐山大地震后,全国各地都开始了地震警报演练。有一天中午,我们在吃中饭,奶奶端着饭碗到对面邻居家串门去了,不一会儿,就传来了地震警报声,奶奶忽然在外面喊:“地震啦!地震啦!快出来!”我们急忙放下碗筷,扶住奶奶坐了下来:“别紧张,不过是一场演习而已!”奶奶定了定神:“刚才我着急地喊你们,饭碗都不知道放哪儿了!”一家人找了半天,最后,爷爷在泔水缸中找到了饭碗,大家笑得前仰后合。
几年以后,我们一家搬到镇上居住,家里不养猪了,泔水缸也就完成了使命。爷爷把泔水缸清洗干净后,放在他的床边,当成储物缸用了。实行殡葬改革的那一年,身为共产党员的父亲为做好爷爷奶奶的工作可谓费尽心思,几次话到嘴边都咽了回去,终于有一次爸爸刚开了口,爷爷就接过话茬:“我和你妈妈是赞成死后火化的,就把骨灰盒放进我床边的那口泔水缸里;再去买个大小差不多的缸,以后再把你妈的骨灰盒放在里面。”这也成了爷爷的遗愿。
爷爷在95岁高龄去世,我们一家人把泔水缸洗了又洗、刷了又刷,吹晒得干干净净。安葬之日,爷爷和早他6年过世的奶奶合坟,两口缸之间用一块木板搭着,寓意着两人生生世世执子之手。